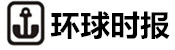本篇文章7890字,读完约20分钟
近年来,人口集中在mainland China、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由此产生的“大城市病”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断讨论。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而应该让人口在城乡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者: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近年来,人口集中在mainland China、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由此产生的“大城市病”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断讨论。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而应该让人口在城乡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教授在论文中逐一批驳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关于大城市人口聚集的流行观点。他引用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当代中国,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它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市场因素起着次要作用。有鉴于此,聂教授认为,控制当前“大城市病”的正确途径是先分解行政权力,然后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最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聂教授特别强调,坚持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在学术上保持“政治正确”,在互联网上可以尽情欢乐,但未必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欢迎讨论。
典型的“大城市疾病”包括:高房价、交通拥堵和过度吸收资源。图为2013年1月25日,北京地铁东直门站,早上高峰时段人群涌动。中国视觉数据(000681,诊所单元)
1.“控制大城市人口”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吗?
近年来,是否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成为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话题有两个有趣的观点。首先,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确反对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从而形成了“一边倒”的立场,这在经济学中非常罕见。你知道,就连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雷戈里·曼昆也承认,“九个经济学家有十个观点。”第二,在政府出台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的背景下,学者们的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政策背景。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特大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相继宣布了地方“十三五”规划,其中明确了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的目标是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上海2500万,广州1550万,深圳1480万。

在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价格引导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全国各城市的经济份额和人口份额应该完全对应,从而实现各城市人均产出的均等化。这实际上是生产要素边际收益相等原则的体现。显然,在理想状态下,政府不需要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只需要让城市自由竞争。

不幸的是,现实并不理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中认为,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或纯粹的计划经济,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在政府不同程度干预经济的前提下,讨论政府是否需要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一个现实问题。
但是真正的问题往往很复杂。如果你问一个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你同意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吗?大约90%的人会不同意。如果你问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大城市病”吗?大约80%的人会同意。如果你问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承认每个城市都有承载人口的极限值?大约99%的人会同意。事实上,第一个问题和另外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但是答案却大相径庭。

可以看出,在是否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问题上,经济学家们的价值观和想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在逻辑和事实上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我想分析大城市人口集聚的内在逻辑和特征事实。
第二,城市层面的影响比市场因素更大
李一宁先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西方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战胜封建庄园经济的过程。我们的团队最近在《管理世界》(2018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城市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表明,中国城市一直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市场扩张的结果。总的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依靠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来实现国家治理。《子·同治简》初云:“天子之职大于礼,礼大于分,分大于名。”什么是仪式?季刚也是;要点是什么?君主和大臣也是;什么是名字?公、侯、卿、大夫皆也。丈夫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人们只服从一个人。虽然他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高度的智慧,但他不敢不跑步就服务。这难道不是一种礼貌吗?”总之,中国古代治国的秘诀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都从中央政府分配给地方政府,从上级城市分配给下级城市。

“秦政治制度一百代”。显然,这种治理逻辑已经扩展到了今天。
第一个例子是财政分配。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体制下,上级资金由中央政府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分配,各级政府通常优先考虑本级的财政需求,这导致下级政府的财政资源被上级政府“剥夺”,但权力在不同层次上向下积累,形成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平等的局面。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扩权强县”、“省管县”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上级机关截留下级机关的财政拨款。

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层面。我们团队的文章“先天优势还是后天努力?——国有企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见《财经》2014年第11期),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但国有企业的水平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安排的产物。国有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其主管单位的行政级别决定其自身的行政级别。比如,中央部委的企业一般在正厅以上,省政府的国有企业最多在正厅,地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最多在正厅。国有企业管理水平越高,获得的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越多,这是其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例子是医院和大学的资源分配。各地区三级医院的数量基本上由该地区的行政级别决定,然后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由该地区不同系统的行政级别决定。例如,一个地级市可以有三个排名前三的医院,但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可以有五个;在每个城市,一般的部门级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和军队)都可以有一个综合性的三级医院。北京作为直辖市,拥有的甲等医院数量(54家)超过了大多数省份的甲等医院数量。根据复旦大学医院管理学院的百强医院名单,北京和上海各有约20家百强医院,占中国百强医院的40%。

名牌大学的分布与城市水平正相关。中国有116所“211工程”大学和39所“985工程”大学,其中北京大学占五分之一。39 985所大学中,大部分位于副省级以上城市,只有4所位于普通省会(长沙和合肥),只有1所(西北A&F大学)位于地级行政区(陕西杨凌)。(杨凌,又名“杨凌区”,成立于1997年7月,实行“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它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家农业高新区。示范区管委会享有市级行政管理权、省级经济管理权和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并享受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

在城市发展的具体方面,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它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市场因素起着次要作用。自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城市从上到下分为五级: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普通省会(12个)、地级市(约260个)和县级及以下城市(3000多个)。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行政权力越大,政策越优惠,财政资金越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水平城市相对于低水平城市的优势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

因此,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下,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人才、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丰富程度,也决定了商业环境、教育和医疗制度环境,从而成为决定城市集聚效应的关键因素。
以副省级省会城市为例,与普通地级市相比,副省级城市可以从上级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凭借大城市的户口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利用省会城市的行政地位成为全省的交通枢纽,这些有利因素进一步成为优化商业环境的条件。在具有网络效应的经济环境中,一个城市只有凭借更高的行政级别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然后凭借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形成正反馈效应。因此,只有了解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我们才能把握城市发展的“牛鼻子”。

安徽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徽之所以被称为“安徽”,是因为明清以来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安庆府”和“徽州府”。1952年,安徽省的省会改为合肥,合肥成为全省的经济中心。在过去的两年里,合肥和芜湖一直遥遥领先,安庆排名第三或第四,惠州(1987年更名为黄山)排名最后。
严格的经济分析证明了我们的猜想。在《管理世界》一文中,我们使用了1999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的数据库,并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行政级别越高,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越高。一般来说,当城市水平提高一个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以提高6%左右。江苏省昆山市是中国百强县之首,其行政级别仅为县级。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昆山成为地级市,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6%,昆山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超过中国90%的地级市!
第二,城市管理水平越高,制造企业的资源错配越严重。当城市水平提高一个水平时,以全要素生产率偏差衡量的资源错配程度将增加约10%。
第三,城市层面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是:行政层面越高,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越多,企业聘用技术人才的优势越大,融资利率越低,地方税收负担越小。与民营企业相比,政府补贴、人才优势和融资便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而地方税收负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外资、港澳台企业。
第四,与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市场化因素相比,扣除固定效应后,城市行政级别约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解释的70%,超过市场化因素的总和。
第三,“大城市病”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分解权力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一方面,人口集聚给大城市带来了劳动力、技术和思想的网络经济效应,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大城市病”,给周边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典型的“大城市疾病”包括:高房价、交通拥堵和过度吸收资源。
以北京为例。
首先,北京的房价长期以来一直偏高。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收入比超过30倍,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四,甚至超过了纽约和伦敦。第二,交通堵塞非常严重,首都往往成为第一个。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北京的平均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广州、上海和深圳的通勤时间接近或超过90分钟。第三,水资源严重不足。自2017年冬季以来,北京已连续三个月无雨,创造了30年来最长的无雨记录。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下水长期被过度开采,这使得很难形成降雨条件。“大城市病”的负外部性也很明显。

首先,地区发展很不平衡。94%的人口居住在“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以东44%的国土上,所有一线和二线城市都位于该线以东。在世界大国中,除了北方寒冷的加拿大,如此严重的不对称城市格局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它导致“虹吸效应”。凭借优惠政策和获得的优势,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零和博弈。当然,凭借行政权力的天然优势,大城市总是赢家,而周边的中小城市通常是输家。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和高铁不仅提高了中心城市的gdp增长率,还降低了沿线中小城市的gdp增长率。位于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省是虹吸效应的一个生动例子。

第三,公共服务不平等。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这里狭义的“公平”可以理解为纳税和享受公共服务之间的基本对等。然而,在行政层级决定资源配置的模式下,城市间严格的行政层级加剧了阶级分化和民族歧视,也损害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政策制定的初衷是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在各个地区更均衡地分配资源,减少负外部性。从理论上讲,实现城市和谐发展有三种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行政主导。由于城市的主要资源来自于行政权力的配置,“钟必须系紧”,行政权力可以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合理的再分配,实现行政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在行政权力沿金字塔分布、资源配置呈倒金字塔分布的情况下,即使中央政府拥有权力,地方权力拥有者也缺乏改变权力格局的动力。说白了,这个方案基本上不可行。

第二个方案是行政指导和市场引导。既然行政权力“误导”了资源的配置,要扭转这种格局,仍有必要首先重新配置行政权力,然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一步是削弱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例如,首先取消副省级城市级别,然后逐步将所有县级城市升级为副省级城市,最后实现所有城市的级别。第二步是在市场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即在经济效率高的地方,允许资源流动,并考虑区域公平。
事实上,这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我认为这是最可行的方案。我主张在大城市的人口管理中,首先要稀释城市的行政级别,然后再放开人口控制。如果每个城市的行政级别相等,行政权力不干预资源的流动,市场自然会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请注意,我说的是减少行政权力对城市间资源分配的干扰,而不是要求直接取消每个城市内的行政权力。

第三种选择是直接市场化。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任何控制人口流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所以人口限制应该完全放开,最好是完全放开户籍限制。这是一种彻底的疗法。但想象一下,如果大城市的人口和户籍限制完全放开,将会发生什么,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首先是过度拥挤,“大城市病”将变得更加严重;其次,无数人追逐行政权力造成的“级差地租”,导致地租消散;最终,它不仅会抑制大城市的活力,还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让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政府在大城市用飞机扔钱,政府可以规定只有在大城市有户口的人才能参与分钱,政府也可以允许全国的人都去抢钱。显然,两种方案都不公平,不能提高效率(确保最需要钱的人得到钱),但是哪个方案更糟糕?显然,是后者,因为它将导致严重的踩踏事件,甚至社会动荡。
经济学中有一种“次优理论”。如果一个分配方案至少有两个条件不满足帕累托最优,那么减少一个条件可能不是更好,但增加一个条件可能不是更坏。不幸的是,在行政权力支配城市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引入完全市场化的因素则完全不同,适得其反。
4.质疑几种流行观点
既然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疗法,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反对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自由主义决定了一些人的观点。其次,它误判了一些基本事实和逻辑。读完他们的文章后,我认为要么他们的论点缺乏事实,要么他们的逻辑不明确,这通常很难说服人们。
鉴于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先生的文章《无法控制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京沪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见2016年10月13日发布的微信公众账号“泽平宏”)观点明确、证据直接,我主要质疑他的以下文章。
流行观点1:发达国家有大城市,所以中国也应该鼓励大城市聚集。这是反对者的主要论点。经常提到的例子有日本的东京都市圈、韩国的首尔都市圈、美国的纽约都市圈和英国的伦敦都市圈。
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然而,应用这一逻辑至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这一现象本身在发达国家是健康的;第二,当这种现象被复制到中国时,它符合中国的国情。
不幸的是,这两个前提是不够的。首先,东京和首尔都面临严重的“大城市疾病”,它们正在建设几个“次首都”。早在2003年,伦敦就开始征收汽车拥堵费,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从而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第二,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主要是自发市场扩张的结果,因此没有必要进行深度的政府干预;中国的城市群是行政权力配置的结果,此时放开市场等于鼓励“权力级差地租”,这更糟糕。我们不反对集聚效应,但我们反对权力产生的集聚效应,防范集聚效应的负面效应。

欧美发达国家成人肥胖率很高,其中美国为38.2%,居世界第一;新西兰(30.7%)、澳大利亚(27.9%)和英国(26.9%)也位居世界前列。所以,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从现在开始它必须增加肥胖率吗?不幸的是,许多人对这种明显的方法论错误视而不见。
流行观点2:解放人口控制对大城市有利。如果放开人口控制,大城市可以凭借优越的资源吸引大量的中青年劳动者,从而缓解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没错,但是你考虑过这种做法的负面影响吗?从一般均衡思维来看,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变化。大城市越来越多,其他地方越来越少;大城市受益,其他地方遭殃。大城市的高房价耗尽了中小城市普通家庭的资源。关键在于,中国的大城市并不依赖公平的市场竞争手段,而是依靠固有的行政层级。以往对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研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城市之间不公平的零和博弈。

流行观点3:北京的人口密度不高,所以交通拥堵可以缓解。这是偷窃的概念。当我们说“北京”很拥挤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在六区或五环路以内,没有人会认为怀柔很拥挤。任泽平先生在文章中还承认,“北京五环路和上海外环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807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为14,525人/平方公里。”北京核心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纽约和伦敦,位居世界第一。那些认为北京不拥挤的人应该在早上高峰时间挤地铁13号线和4号线。毕竟,“当你把它写在纸上时,它总是肤浅的,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市六区”指北京市原中心城区东城区和西城区,原郊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编者按)

任泽平先生又说,北京的城市布局不合理,街道密度不够。没错,但你能改变十多年乃至数百年的城市模式吗?你能在五环路内重塑自己吗?任何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无异于一场白痴梦。
流行观点4:北京不缺水。任泽平先生推测:“到2020年及以后,北京的总供水量将达到49.5-52.5亿立方米(包括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量14.1-17亿立方米),比预计的总需水量多5.5-9亿立方米。”
老实说,我不太乐观。根据公开的消息,我计算出南水北调工程每年流入北京的水量只有9.38亿吨,只有预期目标的55%到67%。尽管北京人均水资源从100立方米增加到150立方米,但还不到1700立方米国际警戒线的十分之一。
还有人说洛杉矶的人均用水量低于北京,所以北京不缺水。北京和洛杉矶在产业结构、节水设施和节水意识方面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说白了,如果一名教师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岗位,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教师都必须身患绝症才能休息吗?
总之,控制当前“大城市病”的正确途径是首先打破行政权力,然后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最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别无选择。坚持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虽然在学术上可以保持“政治正确性”,在互联网上可以尽情欢乐,但可能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应该放下偏见,走出研究,面对现实世界,深入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

本文摘自《聂政治经济评论》。本文由平台/作者授权的金融网站发布。请不要擅自转载。如果你对干货有意见或文章,你愿意为投资者提供最权威和专业的参考意见。无论你是权威专家、金融评论家还是智囊团,我们都欢迎你积极投稿,进入金融网站的著名栏目。
电子邮件地址:mingjia @ jrj,电话号码:010-83363000-3477。期待您的加入!
标题:聂辉华:大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 兼评几个错误的观点
地址:http://www.hhhtmd.com/hqzx/19262.html